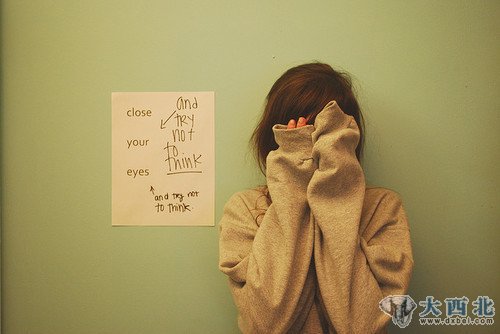
是满月。宏子不时望着心神不定的汉子。他从刚才就猛抽香烟。宏子望着海,夜晚的海没有焦点,心想:为什么会没有一点感伤。不过,思绪也没有持续下去。她觉得死亡不应该不会悲伤,可是她却不觉得悲伤。背后的散步道路每隔五分钟就有汽车经过,车前灯直射到他们两人的低低沙地上。他递出药包,宏子默默接过。他接着打开凤梨汁罐。宏子拿着药包和果汁罐,等他说话。他没有看宏子,先吃了药。
“为什么不吭声?”宏子觉得他的动作有点怄气的样子,望着他问?“还有什么好说呢?”他望着海回答。
“后悔了?”
“不是我提议要一起死吗?”他的语调含着怒气,宏子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
“是啊。不过,我倒觉得你有点勉强。对不起,这样说!”可是,他默默无语。宏子把药粉分两次吃下。分量很多。吃完药,宏子又望着他。月光下,他脸色苍白。宏子心想自己到底是不是爱他,不清楚。但是,他提议一起殉情时,宏子一口就答应了。宏子内心已疲累至极,七年的女侍生涯,五年之中被三个男人抛弃;第六年,相爱的第四个男人却已有妻子。宏子只能爱男人。第三个男人以轻蔑的口气对宏子说:“你只能用身体看东西,最好自制点!”说完,掉头而去。不过,宏子并不恨抛弃自己的三个男人。宏子太正直,总是吃亏。三个男人都很狡猾。不过,他们只要有一点长处,宏子就会爱上。她看见同事个个天生机灵,常常很羡慕的想道:“我难道不能再机灵一点吗?”凤梨汁有六罐,男的喝了四罐。天气并不热,他为什么猛喝果汁呢?宏子不知道,他把报纸垫在头下,躺下去。一小时后,徒步区上,车辆减少了。宏子很想睡,但仍坐着望海。晚上没有焦点的大海很像宏子的人生。为什么不觉得悲伤?她又想了一想,仍然不清楚。没有肉体上的疼痛,我现在不会真的死吧?宏子早就很想睡。男的突然粗鲁地把她推倒在地。她竟忘记他也在这里。宏子觉得自己在遥远的地方跟他相好。她张着眼睛任由男的抚弄身体。仿佛失去了意志,宏子的身子随对方之意而动。她只清楚听到他的询问声:“为什么张开眼睛?”是啊,以前在这种时候都闭上眼睛啊!可是,没有说出来。她仍然张着眼睛。睡意比刚才更浓,她闭上眼睛,同时觉得男的正替自己整理衣裳。你还不想睡?我先睡了,亲亲我好吗……舒适的睡眠似乎来临了。宏子最先看见穿白衣服的年轻女人的笑容。那女人问:“醒来啦?”宏子知道那女人是护士。接着,宏子觉得脑袋有点麻木。她想动动手,仍然麻木,动弹不得。她顿时了解,自己昏睡将死的时候,被人发现,送到医院急救。护士让她喝下果汁。她想:不知道他怎么样啦?不过,她没有问?为什么呢?她自己也不知道。右边的窗子放下了百叶窗,也许是白天。护士走出病房。宏子胃很痛。护士走进来,在宏子的左臂上打针。随后,宏子就睡了。醒来,日已暮。意识比先前清楚多了。百叶窗打开一半;隔着纱窗,可以看到前方的建筑物,也许是医院的玄关,那建筑物的高处可以看到一块写着“德田外科”的大看板。宏子心想,这儿大概是一楼。玄关对面可能是人潮汹涌的马路。玄关旁有三棵喜马拉雅杉,一辆黑轿车。宏子像听音乐一样听着外面传来的杂音,又昏然欲睡。不久,她觉得有人走进来,拿针头刺入右臂。醒来,已到清晨了。一个老护士进来打开百叶窗和玻璃窗,放下纱窗。以碧蓝的天空为背景,宏子又看到了“德田外科”的看板。护士把装果汁的瓶子放在床边桌上,说声:“想喝就喝!”便走出去。过一会,一个穿白衣的中年男子领着年轻护士走进来。宏子知道那是医生。
“能说话吗?”医生问?是沉稳的声音。
“可以。”
宏子挺起上半身,坐在床上,这才发觉自己身上穿着淡蓝的浴衣。医生要护士离开。护士出去后,医生坐在床边圆椅上。宏子突然涌现泪水,轻声说:“是不是他已经死了,我却活着?”宏子低声哭泣。
“比你早醒来,在对面的病房,要不要见他?”医生说完后,宏子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认为他已死。她蓦然止住哭泣,用茫然的目光,隔着纱窗,眺望夏日上午的阳光。白漆的木篱内侧有大理花和向日葵的花坛,一个穿白短裤打着赤膊的少年正在洒水。
“是我儿子。”
医生说。宏子觉得医生很亲切。医生从椅子上站起来,走到窗边,打开纱窗,问道:“小鬼,今天也要到海边去吗?”那少年回过头,眼睛很大,说:“不准到海上去!”也许是模仿父母的说辞。医生笑着回到圆椅,又问一次:“要不要见他?”
“不想见。”
宏子答得很干脆。
“你以前吃过几次安眠药?”
“这是第一次。”
“真的?其实是我的一位年轻朋友,很偶然地发现你们。我这个朋友常因失眠到处行走。昨天清晨四点,他在散步道路时,发现了你们;就到附近认识的人家借用电话打给我。我问他为什么不先通知警方,他说两人都还有气息,最好不要登在报上。于是,我亲自开车到现场,和朋友合力把你们送到这里来。当然,如果救不了,我一定马上通知警方。我觉得最好先把我那失眠朋友当时说的话告诉你。他当时很怀疑地说:他们要死,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呢?”
“你这个年轻朋友现在几岁?”
“三十三岁,比我小十岁,是围棋朋友,为人很好。我叫护士帮忙,把橡皮管从你们两个的嘴巴插到胃囊,让你们吐出安眠药。你们吐得可真狼狈。”
医生停了一下,狼狈相!也许是这样。宏子想像当时的表情,不禁觉得自己很可厌。
“老实说,吐过后,才知道你服下的是超过致死量的巴比妥粉末,而对方服用的只要连续睡两天就可以自然醒来的布罗巴林锭剂。再稍微解释一下,布罗巴林在药店可以公开发售,而巴比妥是用来配药,才研成粉末,只有医生或药剂师可以使用。我处理过许多吃安眠药自杀的,但从来没有遇到过男女双方服用不同药剂的情形。本来应该通知警察,但想起年轻朋友说最好不要让你们成为报纸采访的对象,才搁下未报。对方昨天已经完全好了。我不知道你们的状况,也不必要知道。你以为如何?”
“通知警察的事吗?”
“是的。”
“他知道这件事没有?”
“不,没有告诉他。”
“他说要见我吗?”
“他也说不想见你,只说要尽快离开。”
“就让他走吧。这里的费用由我支付。”
“那就这么办啦。”
医生从椅上站起来。
“我今天也可以回去了吧?” “可以。恕我多言,通常殉情未死的人都不会想立刻再去死。那就让他先回去吧。”
医生向她点点头,走出病房。不久,护士传言说,那男的要一千元搭电车回去。宏子点点头打开枕边的手提包,拿出一张千元钞,递给护士。宏子简直不敢相信。不久就从敞开的窗口看到那家伙站在医院玄关前,他走出医院大门,环视左右,然后以稳稳的步伐挺身走去。宏子觉得爱他竟是这么空虚。她想:我难道竟然缠得他想要杀我吗?一切都这么可恨。宏子冲动得想尽快回公寓去,把沾有他味道的东西全部处理掉。她付清医疗费,向医生和护士道谢,走出了医院。阳光刺目。走出医院就有一家水果店。她付钱买了三个西瓜,请水果店送给医院的护士。再过去不远,就是巴士站牌。穿泳装的男女从巴士车道走过去。宏子想起了医生儿子晒黑的脸。她觉得白色的东西很刺眼。走在自己前面的男人白衬衫、自己所提的白手提包以及自己所穿的白高跟鞋都很刺眼。她坐巴士抵达电车站,买了车票,走上月台,刚好下行的电车抵达,来作海水浴的人随着热气一起被吐到月台上。宏子坐在空空的长椅中,铁道那边立着百货公司和电影的广告牌。电影看板画出了法兰莎。阿努尔阴暗的表情。看板那边是住宅区,闪耀在明亮的阳光下,宏子目眩,想道:“我还活着。”
她用右手拇指和中指按住太阳穴,左右摇了好几次头。手指离开太阳穴的时候,她看见那家伙正倚着楼梯栏杆站立。他左边侧脸对着这边。宏子涌起一股厌恶感。不知为什么,这股厌恶感竟变成想冲喉而出的不快。宏子忍受不住。随着厌恶感的高涨,她不禁对他涌起了一种近乎憎恨的感觉。宏子不想看他,却盯住了他的侧脸。真不敢相信他穿的白衬衫在前天以前是我亲手替他洗,亲自用熨斗烫的;我曾被他拥抱过,曾在枕边互述衷情。宏子仿佛被人用什么粗糙的东西倒刮着肌肤一般。他往这边看,刹那间神情变得紧张凶恶,随即离开栏杆,从人群中往月台后方走去。他的形影看不见时,宏子想道:“这种厌恶感大概会一直持续下去吧!” (责任编辑:鑫报)










